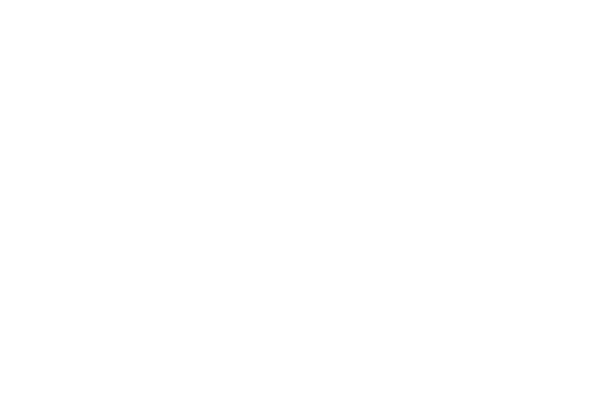講道與釋經(下)研經取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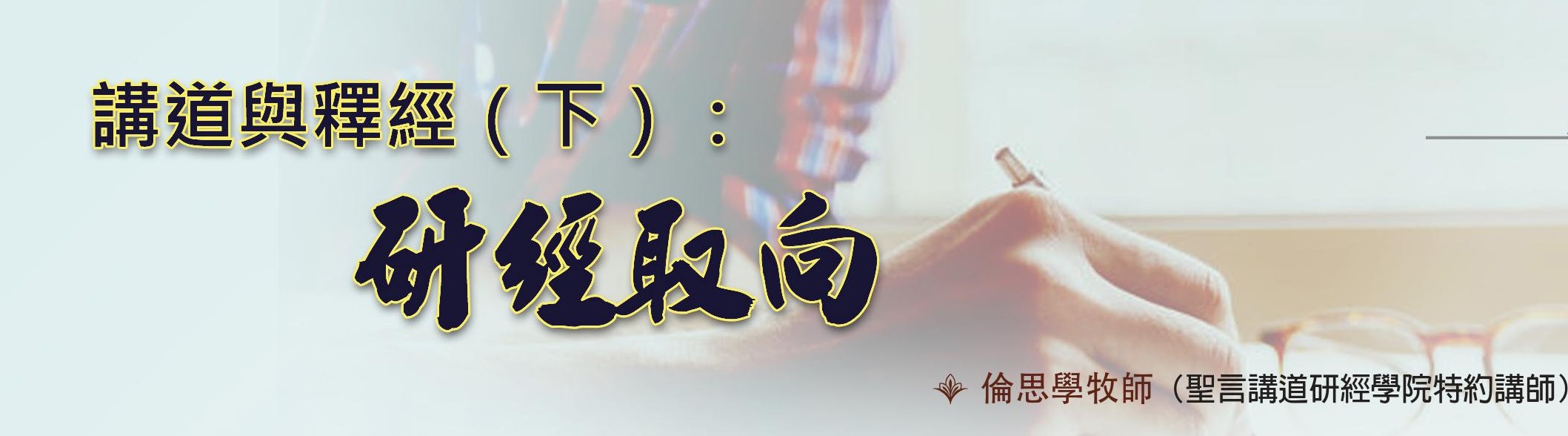
一位講道者最終的任務是宣講神藉着經文的信息來影響聽眾的生命,他要把古舊的經文翻譯成現今能實際應用的信息;透過他的講道橋接着經文世界和現今社會,叫聽者意識到「他(祂)是講及我的現況」或讓他們知道「你就是那人!」(參撒下十二7)。 要完成這任務,講道者必須回答兩條問題:經文的意思是甚麼?(What did the text mean then?)然後,它現在講些甚麼?(What does it say now?)當然,第二條問題的答案是承接着第一條問題的答案,若掌握不着第一條問題的答案,不論第二條問題的答案是如何貼地相關,都未能有把握地表達出神的心意。
八段錦1中的頭三階段就是要回答第一條的問題:經文的意思是甚麼?解經講道建基於對整段經文的徹底解釋。這涉及認定經文的體裁,對經文文字分析研究,確定單詞和語句在聖經時代的含義。當然講道者若能有原文的造詣,就能更準確地掌握到經文意思,但即使他不使用希臘文和希伯來文,他也能藉着神學詞典、個別經卷的註釋書、聖經字典和不同的聖經軟件等工具書的幫助,得出類同的資料。例如網上的新英語譯本 (New English Translation,簡稱NET), 內中的註腳部分就提供了非常實用的原始數據,可減省很多詮釋的時間。2這些對字、詞、句法等的研讀當然不可少,但還是不足夠,我們還須把考據學去蕪存菁淨煉出來的三個語境的分析技巧用來研讀經文。
三個探索經文作者原意的取向:文學、歷史、神學
每一段經文都有它的語境(context),我們必須把它的文學、歷史和神學語境分析清楚,才能徹底明白它的意思。當初文學界引考據學進入教會時,多強調其科學「客觀」批判的本質,所以偏重拆解經文,故把criticism一詞直譯為「批判」、「判別」等,以致堅信聖經權威和整體的傳道人對這些考據方法拒於千里,他們在想:「我們憑甚麼可以批判聖經——神的話呢?」但日子久了,隨着聖經學者多瞭解這些方法時,漸漸覺得其中也有可取之處,就把這些考據方法精粹的地方,納入為解讀經文的三個語境:(一)文學分析;(二)歷史分析;和(三)神學分析。換句話說,這三個分析層面成為探索經文意思的一個整全向度(holistic approach),互補(資料的)長短,彼此平衡和互動,是釐定正確解釋的有效方法。因此,近年criticism一詞也重譯為「考據」、「考證」、「鑑證」、「鑑別」、「評鑑」等,而本文所採用的是偏向中性的譯法——「考據學」。
(一)文學分析
聖經是神透過人而寫成的作品,同時也是一本文學的鉅著,有它獨具的文學價值。經卷的作者就是透過不同的文字、文筆、文體把從神而來的信息傳遞給我們,而當中所關注和研究的包括了文法、文理、文路、文氣、文彩、文心等,是解讀經文必經之路。
文學分析視經文為一個整體的文學單元,看重經文的修辭本質和價值,欣賞它的藝術創作。當我們稱經文所記載的事件為「故事」,這並非指這些事件如小說裏的虚構故事般,而是指作者以故事文學格局來記敍歷史事件的發生。這些記載都是真實的歷史事蹟,只不過是以故事的格局呈示出來:當中有頭有尾、有佈局、有情節、有人物等,把信息帶出來。當遇到經文重複地記載同一類似事件,這也並不意味着是抄襲不同版本或是被接駁編删的結果;確切的是,作者使用重複或重疊的修辭技巧,為要突顯某一個真理。很多敍事的經文是先經過一段口傳的日子,到後來才被人記載下來,而重複或重疊是口語版本強調信息的其一方法。至於遇上同一事件,而不同作者有不同的記載,也不一定是記載對錯或版本真假的問題(只有一個是真實事件,其餘的是作者因某些緣故擅自修改),其實是作者刻意挑選詞𢑥和鋪排材料,以針對他那特定的聽眾,為要達到那特定的神學目的。
經文的體裁類型深切影響經文的解釋(以及宣講時的語調),因每一類型的體裁都有其各自一套屬於自己的解釋程序、方法和規則。如敍事體的經文關注的是情節、場景、佈局、人物、角色的素描等,它以人物和事件的發生來推進作者的意思和意向;而詩歌體的經文,多以修辭文彩、影像語意來激發我們的想像力,帶出意境和意思。我們只要細心閱讀經文,不難發現聖經的記載方式豐富,完全超出了我們的想像。事實上,沒有一個簡化單一的方法,能叫我們完全掌握到所有不同體裁和經文類別的意思。因此,認識不同經文體裁能加強我們對經文的體驗,提醒我們可以期待找到的內容。這種認識有助我們意識到經文的動力、能正確地與經文相遇(encounter),且宣講時能提供合宜的關注和有效的溝通渠道。
釋經講道的前提是重視經文作者所看為重要的,對講道者來說,作者記載在經文中的一字一句都是很重要。我們必須注意經文(語言)的修辭、風格和獨特資料,而這些文彩都可從聖經的每一頁看出來,它們能夠幫助我們找到潛在的解釋線索;因此,在講解時不單要處理它們,更要對聽眾交代清楚它們在經文中所扮演的功能。例如,在馬太福音十九章30節出現的「有許多在前的,將要在後;在後的,將要在前」和二十章16節出現的「在後的,將要在前;在前的,將要在後」,這兩個相似的句子中間夾着「進葡萄園工作的工人比喻」,講道者講解時必須把這包着一頭一尾的修辭特色交代清楚,否則未能盡善地把作者想表達的信息發揮出來。換句話說,要正確地解釋這比喻,必須清楚交代這前後互相呼應的兩節經文,若比喻的解釋未能解通這兩節經文,就表示那不是比喻的正確解釋。
大體上,教會在傳達聖經的神學內容方面做得很好,但對經文的文學(特別是修辭的一部分)關注仍有待改善,好讓它能在會眾的想像中活躍起來。一位善解經文修辭的講道者,若能採用類似的修辭技巧在他的宣講中,就可以原汁原味把作者的信息傳達出來。例如,書信是以邏輯理據來推進,講道者也就按理據來推動和發展;詩篇是透過平行概念和影像引出信息時,講道者宣講時也多宜以概念和影像來表達出詩體的真理;記敍文既由故事 / 人物 / 事件等組成,宣講時也要看重佈局、情節推展、人物素描等安排,把經文信息帶出來。
大部分傳道人在神學受訓期間,沒有接受過宣講修辭學方面的裝備。當然,神學院都會讚歎聖經的修辭價值;或許也在釋經學科中教授修辭學,但在程度上,那只不過是釋經學科內的其中一個專題,目的只是確保同學接觸過這些修辭方法而已。在講道學中更罕有在這方面的實際具體裝備,讓學員日後可在宣講中有系統和規律地採用這些修辭技巧。因着傳道人對宣講修辭意識的疲弱,故沒有觀察注意到有影響力信息中的修辭技巧。往往他們只注重了這些模範講道的內容,以致仿效時只是內容的抄襲,删減了當中的修辭技倆,難怪他們的信息影響力不及所仿效的講道。但若他們能關注到經文中的修辭和文學,仿效這些修辭技巧和文學特色,應用在他們的講道裏,那就能補足求學時期沒有關注到的。
懂得經文的文學結構,就懂得從宣講該段經文的前後內容中找出支持的理據來襯托那要傳遞的信息。例如,講解馬可福音十二章40至44節寡婦奉獻的兩個小錢,可從它的文學情境、上下文理中找出數個她不奉獻的合理藉口:其一,「我實在很窮,需要這兩個小錢。反正按摩西條例,我理當是受賙濟那一位」;其二,「請看,聖殿多麼宏偉!(可十三1、 2),我所獻上的微不足道,無補於事」;其三,「你且看這些文士敗壞的品行,他們侵吞了我們的家產!還要我奉獻給他們?」(十二38-40)這三個從上下文理中蒐集而來的藉口,配合講道的發展,豐富了當中的內容,強調了寡婦堅持把僅有的獻上是因為她知道奉獻是對準神而作,不是因人而為。從文學角度來看經文,可察覺出作者如何把不同的故事 / 事件鋪排串連在一起,呈現在讀者的眼前,讓他們檢測到經文要傳達的信息。
當我鼓勵講道者善用「修辭技巧」時,這並非指花言巧語、智慧的言語(林前一17)、高言大智(林前二1)、智慧委婉的言語(林前二 4)等,它是指口語以重複、映襯、重疊、同音、同義等的修辭技巧,以及說話的先後,漸進地揭示真理,讓聽眾易懂易明並易於接受信息。以文學分析經文,不單只看重經文的內容,更注意到作者如何表達和鋪排他的材料,以致可以仿效這些修辭技巧並應用到講道中。
文學分析一定要配合歷史分析和神學分析才能定準經文的意思,它不能單一獨存、獨立地運作。畢竟,文學分析是對經文文本的研究,當文本脫離了歷史的框架或沒有了神學的根本認知和方向時,這樣的研讀往往會誤解了作者的原意。以兇惡園戶的比喻(太二十一33-39)為例,若單從文字、文學來解讀經文,而忽略了耶穌講這比喻的歷史語境並作者把這比喻放在這卷書裏的神學目的,我們可把它解讀為人性的敗壞——因貪財,不惜一切甚至殺人,以霸佔別人的產業。當然,這樣的理解也可成為一面鏡子,讓我們可以檢視自己(有否為了滿足自己而侵犯了別人的權益?),帶來自我警惕的道德應用。但這樣的解讀卻不是作者在馬太福音記載這比喻的意圖,它更未能交代清楚比喻當中的許多細節部分。如此把這比喻純文學地孤立讀出來,就是把神的話語貶為《伊索寓言》——每一個故事都是獨立的,旨在提供德育上的訓勉。這樣的解讀,無疑藐視了耶穌講這比喻時的歷史情境,以及作者的鋪排、整書卷的文學創作及其神學目的。這段經文正確的解釋應當是:作者講述耶穌與猶太的宗教領袖的衝突,耶穌藉這比喻指出在神啟示的歷史中,他們不但沒有聽從先前先知的勸戒,更拒絕祂,甚至要殺害祂。
如此看來,單有文學分析未能正解經文,必須加上歷史分析和神學分析,才能互補長短。
(二)歷史分析
歷史分析的起點是:聖經所載的都是歷史事實,不同作者的記載,因觀點、角度、寫作對象、目的不同,以致細節內容或許會有不同。聖經是根據事實寫成,並非虛構出來的。耶穌確實在二千多年前在伯利恆出生,在巴勒斯坦一帶趕鬼、治病、宣揚天國的福音,且被釘死在十字架上。歷史分析是將經文置於其歷史環境中,從當時歷史、文化、社會、習俗等角度去解讀經文。那就是說,歷史分析是認定作者在某一時空中寫成書卷,有他要達到的特定目的。如此,講道者要重建作者的意圖,就要瞭解書卷的作者是誰、是寫給誰的、在甚麼的情況下他寫下這些經文,以及他期待當時的讀者怎樣回應他所寫的。
這樣的歷史分析容讓我們窺探到記載這些經文時期的歷史情境,察驗出當時催迫出來的氣勢,並能順着這氣勢來解釋和宣講這段的經文。以提摩太後書四章1至7節為例,這段就把全卷提摩太後書在歷史中寫作時的動力,淋漓發揮,特別是「我在神面前,並在將來審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穌面前,憑着他的顯現和他的國度囑咐你……」(1節)和「我現在被澆奠,我離世的時候到了……」(6節),把整個寫作語境因由清楚地呈現出來,讓讀者體驗到保羅當時的嚴肅、迫切和關愛的交錯心境,催迫着他勸勉年青的牧者提摩太着重牧養中最要緊的傳道任務。又申命記中的一句「你們要聽從他」(申十八15c),也可藉着對整卷申命記寫作時代的歷史分析,讓我們意識到「神是藉着祂所揀選的代言人來治理和領導祂的子民」。因申命記所記載的事蹟,大部分都在五經中的前三卷書(出埃及記、利未記和民數記)中已記載下來,唯一加進去的是講述摩西將臨的死亡,不能與選民一同進入迦南美地。細看下,我們不難發覺申命記全書首尾各有三章瀰漫着摩西的死(申一37-38,三21、23-28,四21;三十一2、14,三十二48-52,三十三1),每次當提及約書亞是摩西的繼承人,也意味着摩西的離世在即。如此,對一生跟隨摩西、受他帶領的以色列人來說,便產生了一個領導的問題:在摩西離去後,他們怎樣繼續體驗神的恩典和領導?過去有摩西領導他們,當摩西領他們向東行,他們就向東行;他說向西行,他們就向西行。但現今摩西不在了,他們作為神的盟約群體應如何繼續體驗神的恩和跟隨祂的領導呢?從這角度來看,申命記是摩西的遺書,是他臨別的贈言,是他教導以色列人如何在神的話語下繼續履行神與他們所立的約。摩西對他們的指示是:神會在他們弟兄當中興起先知像他,並且神會藉着先知所傳講的話來繼續管治、牧養和領導他們,而他們的責任是聽從將來之先知的指示而行(申十八15-19)。如此的歷史分析,營造了一個局勢,為經文定下基調,界定了經文可有之解釋的範圍,這是研讀每段經文當要取的向度。
這裏歷史分析是指研究一段記敍歷史的經文(history in the text),而不是指傳統文本考據或編纂考據中的研究一段經文的記敍歷史(history of the text)。雖然兩者之目的同是要確定實際發生的事情,但所採用的方法和前設完全不一樣。3歷史分析是把經文鎖定在事件發生的歷史時刻,按當時的人物心態、政治局勢、社會習俗、宗教信念、風土人情等來理解經文的意思。如耶穌的一句:「你們看我的手,我的腳,就知道實在是我了。摸我看看!魂無骨無肉,你們看,我是有的」(路二十四39),我們就當把它解讀成:
(1)作者路加是把歷史的事實記載下來(路一1-4),他是事件發生時期的同期人物,認識那時期的人,能對質他所聽所聞和所蒐集的一切資料。
(2)路加是一位醫生(西四14),是一位有識之士、一位學者,按理是位有信譽的人。經他檢證後,這是事實的真相——復活的耶穌向在耶路撒冷聚集的門徒顯現,對他們說出這句話。
(3)那時這班心裏愁煩的門徒看見主顯現,就驚慌害怕、心裏起了疑念,以為他們所看見的是魂(路二十四36-38),而耶穌就安撫他們,說出這句話來。若繼續看經文,耶穌更在門徒面前吃下一片燒魚,證明祂是有骨有肉的,是身體的復活。
(4)除了路加所記載外,我們還有其他的歷史資料證實耶穌的身體復活了。
(5)路加福音約在主後60年寫成,對象相信是給那些有希臘文化背景的人,方法是按着次序寫成,目的是把真實的事情記載下來。
當我們把經文置於其歷史環境來解讀時,所關注的歷史有三個層面:
- 經文事件發生時的歷史層面:事件的發生。例如,摩西在約旦河東(申四41)對以色列眾人(申五1)的訓勉。
- 作者記下事件時的歷史層面:作者記述事件、成書時的寫作目的。例如,申命記的作者寫成申命記的時刻,留下申命記給那時代的以色人。
- 神整體啟示計劃的歷史層面:這段經文在這書卷中所扮演的角色,又這書卷在全本聖經正典中的角色。這層面趨向神學分析的解讀,是從整體啟示角度來看經文。
這三個歷史層面都支配着經文的解釋,它們都是同等重要,不能忽略其中一個層面。雖然不同歷史的層面可引帶出不同的信息,豐富了我們對經文的認知,但解釋時三個層面是互動着的,必須彼此配合相容、彼此協調。在下期介紹第三階——經文目的時,我們會有進一步的探討。
(三)神學分析
從文學分析和歷史分析,我們可解讀到經文白㡳黑字所載的內容和字面的意思,而我們還須要進深一層從聖經神學觀點去理解經文所講的,才領受到神要傳達的信息。舉例來說,單單知道耶穌是在午正與撒馬利亞婦人談道,其後又領她和全城的人信祂為世人的救主(約四1-43)的歷史資料,不會對我們的生命有甚麼影響。經文是須要透過神學分析才能進到權威應用的層面。
神學分析就是當我們對經文內容有一正確的理解後,去追問從這段經文中我們認識些甚麼關乎神的事情──祂的屬性、祂的作為、祂與人之間的關係等。聖經寫成的最終目的不是叫我們知道歷史中發生過甚麼事情,而是神透過這些經文記下來的歷史,讓我們認識神,繼而讓我們懂得如何調配自己的生命和生活,去經歷、領受祂的恩寵並配合祂的計劃。因此,我們要藉着神學分析看出,神是通過耶穌與撒馬利亞婦人談道的一段事蹟讓我們認識到:
(1)神是世人的救主(世人:不論種族、社會地位、學歷、宗教背景;參約三1-16)。
(2)任何人在神眼中都是重要的。
(3)救恩是從基督而來。
(4)神是一個靈。
(5)神尋找那些用心靈和按真理敬拜祂的人(在約四23尾句和合本譯為「要」的字,希臘文原意是「尋找」的意思,故最後一句應當譯為「因為父尋找這樣的人拜祂」。
(6)神的工作不受任何時間、環境、人的期待所限制。
經過這樣的神學分析後,我們才能正確拿捏到作者的原意,所衍生出來的應用才會內嵌着權威。同時也避免了小題大作,摸錯作者的心意,把經文枝節的部分或單按字面的內容而作出應用,例如提出以下似是而非的論調:「一對一個別傳福音是最有效的方法」、「傳福音的三部曲是(1)引起需要、(2)指出罪行、(3)相信基督」等。這些論調當然是有提醒、參照的功用,但卻非作者記下這段經文所要傳遞的信息。
畢竟,聖經(經文)是從神而來,要傳遞的都是關乎神的事情,非「我」的事情。它的寫成,為要叫我們認識神並知道怎樣能與祂有一個好的關係。它本質上不是一本教人自我增值的書本(如「怎樣做一個好父親?」);它是一本神學的作品,故此我們斷不能忽視它的神學價值,而把經文道德化(moralize)、心理化(psychologize)等,繼而進行解讀或應用。道德化的例子:把尼希米記讀成今日作領袖的規範,或把路得記讀成今日婆媳關係的圭臬;心理化的例子:把路得解讀成一位過分依賴家婆的寡婦、大衛王在中年時面對誘惑的失敗、撒該因個子矮小的自卑心態而懼怕與人接觸,或浪子因缺乏母愛的滋養而放縱。這些人物事蹟被記載下來,不是要叫我們以這些事作心理學的個案來研究;他們的事蹟在聖經中出現,是叫我們認識神,從祂與以色列人立約的歷史去瞭解祂是一位怎樣與人交往的神,又從祂獨生子降世去瞭解祂如何藉着天國的福音拯救人類。這是神學分析的起點、基本的認知,是研讀經文時不可或缺的。
按這樣的理解,就會明白到經文的功能;而當中所記述的事蹟和人物行為並不一定代表着有神的認可或認同,是我們須要參照跟從的。因此,神學分析的另一個功能是防止我們把所有的經文都常規化(normalize)。例如,把使徒時期教會凡物公用(徒二44-45,四32-35)解讀成今日所有信主的人都要變賣一切,或是把耶穌要求那少年富有的官變賣一切、分給窮人,去跟從祂(太十九16-22;可十17-22;路十八18-23),解讀成不可擁有個人物資來跟從主,這樣就是誤把經文常規化了。如此看來,神學分析賦予我們推論作者原意的基本方向和必需有的框架。
結語
綜上所論,研讀經文時,我們要從經文中選取完整的思想單元,透過文學、歷史和神學分析,找出作者的神學目的──他記下這段經文要傳遞關乎神的信息。而透過這記載的事件,我們對神的性情和作為有怎麼樣的認識?對神有認識之後,又當如何回應神並配合祂的計劃?文學分析和歷史分析提供了解釋經文的線索,而神學分析則帶給我們解釋的方向,助我們找出作者的原意。前兩者主要是向後看的,參看歷史情境和文學情境而述說出經文的內容;後者是向前看的,是追索作者要傳遞關乎神的信息,因而看出神對我們的要求。我冒着過分簡化的風險,綜合以上三個取向為:透過歷史分析看出事件的發生,透過文學分析看出作者所使用的技巧,而從神學分析則看出經文寫成之目的。當然,這三個分析取向是不斷互動着的,循着各所提供的解釋線索,彼此配合,相輔相成。在下期,我們會進一步看神學分析的步驟和一些與經文目的相關的課題。
附註
1 參《聖言通訊》第二十八期,2018年2月,頁11-13。
2參 https://netbible.org/bible/;瀏覽於2019年6月12日。
3所有關乎文本等的考據一定不能與成書時的歷史實體脫鈎,像編纂考據一樣:它的前設
是聖經乃歷史悠久的作品,經人按當時社會的時需不斷纂改而成為今日的版本,因而
把耶穌聖化為基督,正如中國人把關雲長奉為關帝,把丘仲尼奉為孔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