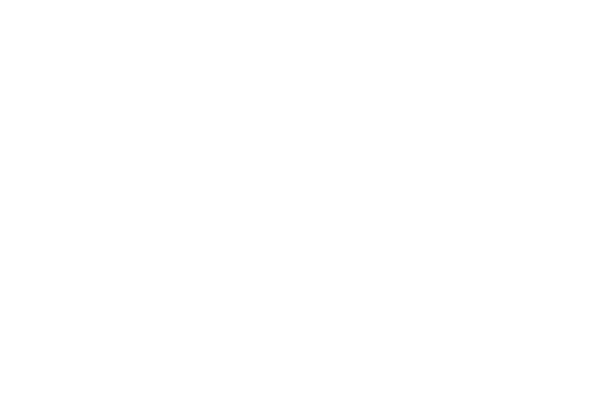聖經中有那麼多看來矛盾的地方,我怎能相信它是可信的呢?
![]() 我曾強調,聖經是神默示的聖言,是毫無錯誤的。但為甚麼有人從聖經中找到那麼多看似矛盾的地方?我們應該怎樣回應呢?
我曾強調,聖經是神默示的聖言,是毫無錯誤的。但為甚麼有人從聖經中找到那麼多看似矛盾的地方?我們應該怎樣回應呢?
讓我從三方面來回應。第一,聖經不是一本科學教科書,但聖經所記述有關科學的資料都是準確的。自從有人類歷史以來,人對天上的群星就有一種特別的嚮往,也許是因為天上的星傳述著一種說不出的奧祕,讓歷世歷代的人都充滿好奇,不斷地研究與觀賞。我們晚上出去看夜空,也會有一種很特別的感受,所以,有人會研究天象、占星等,而中國人的占星又跟外國人的不一樣。星星實在可以使人著迷。
以前的人,憑著自己的理解,去數算天上有多少顆星星。曾有人認為,能被人肉眼看見的星星大概有4000顆。埃及人多利買 (Ptolemy) 說,天上能看見的星星有1056顆。另有一個名叫開普勒(Johannes Kepler) 的人指出,他能數的只有1005顆。再有一位叫布拉赫(Tycho Brahe) 的說,是777顆。不同的人從地球不同的角落,會數出不同的數目,而且連個位數都能數算出來!
以前的人不知道有銀河系、太陽系,沒有今日種種天文學的知識,只憑著肉眼觀察到的天象,就以為我們所見的天空就像是個天花板,掛著一些星星;又認為地是平的,下面由四頭巨大的猛獸頂著,牠們打個噴嚏就會地震。古代的人這一類千奇百怪的理論多的是,因此也有不同的人數算出天上星星的數目。我們要瞭解,那是因為在科學不太昌明的時代,人們沒有現今的天文學知識,便以為星星彷彿是掛在天花板上,有固定的數目。
但聖經的作者怎樣說呢?天上的星有多少?能不能數?他們都異口同聲說,天上的星是不能計算的。
耶利米告訴我們:「天上的萬象不能數算,海邊的塵沙也不能斗量。」(耶三十三22)此外,神應許亞伯拉罕,他的後裔要多如天上的星、海邊的沙。若按照當時的人的觀念,星星的數目大約只有四千,那麼亞伯拉罕的後裔就只有四千嗎?按照古人的觀念,實在不大可能寫出「天上的萬象不能數算」;人憑著肉眼,能知道天上的星是不能數算的嗎?若不是出於神的默示,聖經的作者實在難以有這樣的結論。
再看哥林多前書十五章41節,保羅說:「日有日的榮光,月有月的榮光,星有星的榮光;這星和那星的榮光也有分別。」(“One star different from another star in glory.”) 從前的人怎麼知道星星各有自己所發的光輝?保羅的意思是說,每一顆星都不一樣,榮光亦不一樣。這樣的觀點,在當時的人來說實在是匪夷所思的;但從現今天文學的角度就可以瞭解,每顆星都有它特別的身分(identity),是可以辨認的,一看就知道!
所以,聖經雖然不是一本科學教科書,但聖經所記述有關科學的資料都是準確的。
第二,聖經常採用一些「現象用語」。首先,舉「日出日落」一語為例,有人說:「『日出日落』這說法並不準確!」我們得明白,聖經常會使用一些現象用語(phenomenal language)。若說這種講法不符合事實,那為甚麼現代人也同樣說「日出日落」呢?因為這只是一種表達的方式,表達我們所看見的現象。
詩人說:「它〔太陽〕從天這邊出來,繞到天那邊」(詩十九6),也是現象用語。傳道書一章5節的「日出日落」,也是現象用語。聖經是用普通人能明白的用語(現象用語)寫成的。「日出日落」其實是指太陽運行的軌跡與路線,航海的人或須按天象計算時間的人,也約定俗成地接受了這描述的方式,根本無須用科學方法來鑑定和檢視這說法,否則就會失去一般語言的功能與意義了。
舉一個例子便可以說明這一點。有一次,夫妻二人在夜間談話,丈夫說了一句「夜半三更」,妻子回應說「夜半三更」這講法是錯誤的,夜半其實只有兩更半,不是三更。二人就吵了起來。丈夫說,這是一直以來的說法;妻子說,一直以來的說法是錯誤的說法。丈夫說大家明白就好了;但妻子說,這說法與事實不符,要改正過來。最後爭到面紅耳熱,丈夫看爭不過妻子,就舉起拳頭作打妻狀。妻子見事態嚴重,就大聲喊著說:「救命啊,有人夜半三更要打人啊!」丈夫收回拳頭說:「原來你是贊成我的說法的,為甚麼不早說?」
其次,舉「天有柱」為例與大家談談。天有沒有柱子呢?約伯記二十六章11節說:「天的柱子因祂(神)的斥責震動驚奇」,有人因此質疑說:「天哪有柱子呢?」那麼,這節經文是否與科學的觀點互相衝突呢?
是的!天確實是沒有柱子的。不過,詩人看到群山高入雲霄,穹蒼覆蓋大地,為群山所托住,就好像天有柱子一樣。它可以是一種現象用語,或詩意的象徵性用語。就如中國人說:「天圓地方」,這也是一種從現象出發,按人的感官認識而作出的描述;即使現代人知道天不是圓的,地也不是方的,也無須將它矯正過來。因為這些都與科學無關,純粹是一種修辭學的用法,不必矯枉過正呢。
第三,聖經中的「衝突記述」,往往是從不同角度報道所致。譬如說,馬太記述耶穌出耶利哥城時,遇見兩個瞎子(太二十29-34),馬可卻寫下「有一個討飯的瞎子,是底買的兒子巴底買,坐在路旁」(可十46),另外,路加說:「耶穌將近耶利哥的時候,有一個瞎子坐在路旁討飯」(路十八35-43)。關於事件發生的時間和地點,馬太和馬可都說是耶穌「出耶利哥」的時候,但路加卻說是「將近耶利哥」;馬太說是兩個瞎子,馬可和路加都說只有一個。到底是出耶利哥還是將近耶利哥?是兩個瞎子還是一個?
原來,很多時候我們報道一件事,會從不同的角度去描述。就如現場確實有兩個瞎子,因此便有報道說是「兩個瞎子」,但兩個瞎子之中只有其中一人求耶穌幫助,故另一個報道便只集中在這位求耶穌幫助的瞎子身上。這樣的例子,在今日的生活中依然俯拾皆是。比如你跟別人說,某天你在香港碰到賴牧師正在和陳弟兄一起吃飯,暢談聚舊;但另一位弟兄談及同一件事時則說,他見到賴牧師在餐館裏,和兩位朋友相聚並一起吃葡國餐。到底賴牧師是跟陳弟兄一起,還是跟兩個朋友在一起?他們是在吃飯還是吃葡國餐?其實兩個人的描述都是正確的,只不過角度不同而已!
至於到底是進耶利哥還是出耶利哥的問題,就更有意思了。原來耶穌時代的耶利哥城,有新城和舊城之別,一個叫舊耶利哥,一個叫新耶利哥,二城中間有一條馬路將兩者連貫起來。世界上有許多地方或城鎮,也有新城、舊城或新鎮、舊鎮之別,因此並不稀奇。而今日的耶利哥,只有昔日的新耶利哥城,舊耶利哥城早已成為廢墟了。
因此,馬太和馬可的記載,很可能是指耶穌出了舊耶利哥,進入新耶利哥,或相反是從新城進入舊城,所以兩個福音書記載耶穌是出城,而路加則記載祂是靠近耶利哥。至於這位瞎子,他很可能是在兩個城區中間的馬路上遇到耶穌!這樣,三卷福音書的描述不但無矛盾,而且反映出當時耶利哥城真實的情況。事實上,聖經中有不少報道,也是從不同角度出發所作的記述,並非矛盾。
讓我以馬克吐溫的一句話作結。他曾說:「聖經中我不能理解的地方,不會令我感到不安;那些我能理解的,才令我感到不安。」馬克吐溫的意思是,那些我們不能理解的聖經難題,不會真正構成甚麼困擾我們的問題;但那些我們已經理解的,心中就理應有一種道德的責任感,將它實行出來,應用在生活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