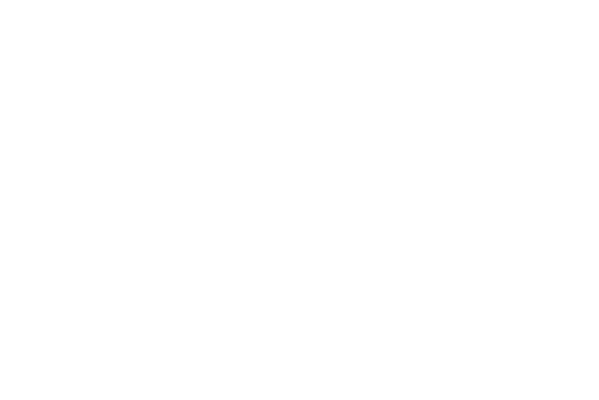您能否想像站在聖地的地土上,重溫 神在聖經中所彰顯的作為,一幕一幕地展現在眼前;又想像與主耶穌一同坐船過渡加利利海、走上苦傷道(Via Dolorosa)、在提比利亞海邊被重新託付…的感受嗎?感謝主,最近讓我們九十二人能有以上的經歷。這實在是 神的恩典。
自從一九九五年第一次到過聖地之後,就愛上了這片地土。我對它的這份愛不是因為它景色比別處優美;不是因為它氣候宜人;亦不是因為它政局安定。我對它的愛乃基於一個簡單的理由 – 因為神大能的作為曾在這地方彰顯;而且我的救主耶穌亦曾在此留下佳美腳蹤。因被父神與救主耶穌那份恩情的感召,自然而然地愛上這片地土。
我第一次到聖地考察與達拉斯神學院九位校友與兩位教授一同用八天時間暢遊聖地,在教授的講解與帶領下獲益良多。還記得在最後一晚的見證會上,大部份牧者都異口同聲說日後要好好研讀聖經,我亦是其中一人。為甚麼我們這些對聖經已有認識的牧者會這樣表示呢?因為在腳踏聖地之後,多年來對聖經的瞭解就像約伯所說的一樣:「我從前風聞有你」;從而決心要鑽研聖經,務求達到「親眼見你」的地步。經過這次旅程,我發現聖地的「地圖」已或多或少印在腦海裡,使研讀聖經時有活潑的「圖像感」。並且決意在日後有機會的話,可以帶領弟兄姊妹到聖地去實地學習
感謝神的恩典,【聖言資源中心】與【加拿大證主協會】合辦的聖地靈修學習團(十月十六至廿八日)已經完滿結束。這次的旅程得以實現,除了要感謝 神各方面的安排與預備之外,還要多謝弟兄姊妹的參加。雖然在行程中有些阻滯 – 如團友上西乃山時扭傷,感冒生病等;然而 神的恩典卻在多方面幫助我們(林後十二9),使眾多團員在回來之後都表示在靈性上有眾多的學習與更新。
Category: 賴若瀚牧師文章
用屬靈偉人的禱文學習祈禱(二)
自從對屬靈偉人的禱文產生濃厚興趣之後,我就是要開始尋索、搜集屬靈偉人的禱文,藉此幫助深化自己的祈禱生活。我經常到半價書局去流覽,在注意郵購書局的介紹,果然有不少的發現。在短短的兩年,我搜購了一百多本的禱文集 – 有古代的、有近代的;有個人的、亦有集合各家而編成的,只是中文的禱文集並不多。
在搜集的過程中,我挑選一些較有深度、又能感動人的禱文,將它們繙譯成中文刊載在所牧養的教會主日秩序單上。後來得弟兄姊妹的鼓勵,分別在一九九六與九八年出版了兩本的繙譯的禱文集:《旋風中的靜語 – 安慰禱文集》與《寶座前的心曲 – 感恩讚美禱文集》。自此之後,閱讀、默想與繙譯禱文已成為我屬靈操練的一部份。
記得有一次繙閱德國神學家潘翟華(Dietrich Bonhoeffer)所著的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中譯本:【獄中書簡】)一書,被他一篇在牢獄中的一篇禱文:【助我禱告】所感動。後來將它繙譯出來,讓我深入體會這位神學家在為信仰下監時的心路歷程:
神啊!清晨我要向您呼求,求您助我禱告,
讓我的思想專注在您身上,因我不能獨自承擔。
我心裡昏暗,有您就有光明;
我感覺孤單,您卻永不離棄我;
我心靈軟弱,有您就有力量;
我內心掙扎,有您就得平安;
我心裡充滿怨恨,有您就能忍耐;
我不明白您的道路,您卻知道那一條路最適合我。
天父啊!
我讚美、感謝您,賜我平靜的一夜,
我讚美、感謝您,給我新的一天,
我讚美、感謝您,賜我您一切的美善,以及您信實可靠的應許。
您已賜給我眾多的恩典,現在,讓我從您手中接受苦難吧!
您必不會將難擔的擔子,放在我的頭上。
您使萬事都互相效力,叫您的兒女得著益處。
主耶穌啊!您曾像我一樣,經歷窮乏、困苦、被棄、被囚;
您嘗過人間的苦痛,當所有的人都離棄我的時候,
您仍在我身旁,您不撇下我,卻尋找我,
您要我認識您,歸向您,
主啊,我願應您的召喚,跟隨您,求您幫助我!
聖靈啊!求賜我信心,保守我不陷入絕望之中,救我脫離肉體的情慾;
求您將愛您、愛人的熱情澆灌在我心,不讓任何的憎恨與怨毒侵擾,
賜我盼望,救我脫離恐懼與膽怯。
聖善、憐憫人的神,我的創造主、救贖主與審判的主啊!
您認識我的本體,亦知道我所行的一切,
您痛恨罪惡,不論貧富貴賤、今生或來世,您都予以懲治;
然而,對於那些誠心懇求赦免的人,您卻樂意饒恕他們所犯的罪。
您喜愛良善,
在今生,您賜人無愧的良心,
在來世,您賜下公義的冠冕。
我想念我所愛的人,與我同囚的人,以及在這房子裡忍受辛勞的人,
主啊,求您施行憐憫,助我更新,重獲自由!
讓我能活得好,無愧於心,在您面前亦坦然無懼。
主啊,無論今日的際遇如何, 讓您的名得著榮耀。
(譯自 Dietrich Bonhoeffer,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p. 88-90)
潘霍華當時為他的信仰,被德國納粹黨囚禁在牢獄中。他面臨死亡的威脅,仍向神發出敬拜,而且心中沒有怨毒,更為周圍的人代求,這是值得效法的榜樣。這禱文特別對當時教會受大車禍影響的遭遇大車禍,更顯出它的寶貴。
習題:請再細心閱讀潘霍華的禱文,並省察您現時的屬靈光境。請問:這禱文如何幫助您勝過環境所帶來的負面衝擊?
(待續)
十步研經法示範6 – 使徒行傳一章八節
第五步驟:逐題解答(三)
讓我們繼續解答第11題至第15題
11. 作「見證人」是甚麼意思?要見證些甚麼呢?
• 這裡的「見證」原意是「見證人」的意思。簡單來說,「見證人」是曾親眼見過,親身體驗事件的發生,又願意將所經歷的一切告訴別人的人。「見證人」必須忠於所見的事實,不可將事實與猜測混為一談,更不能因為利益而放棄真理,亂作假見證。(詞的意義)
• 因此,門徒不單要作口傳的見證,更要用他們的生命印證所說的真實。(詞的意義)
• 作見證的內容包括耶穌的一生,祂的事蹟、祂的死與復活,透過聖靈的力量見證神的道與祂的大能。在使徒行傳的多篇講道中,以彼得為首的使徒經常題述上列的重點,最重要的當然是福音的核心 – 耶穌的死與復活(參林前十五3-4),證明祂是舊約應許要來的彌賽亞。(以經解經)
12. 為甚麼作見證需要有來自聖靈的能力?
• 聖靈要降臨在門徒身上,他們就著能力。聖靈所賜的能力是見證人必須具備的動力。(上文下理)
• 要說服人接受耶穌的救恩,不是靠人智慧與口才,必須靠聖靈在人心裡動工。因為主耶穌曾說,聖靈來是「要叫世人為罪,為義,為審判,自己責備自己」(約十六8)。(以經解經)
• 在使徒行傳第二章彼得講道之後,會眾扎心、悔改,最終帶來生命的改變,這些都是聖靈的工作。(以經解經)
• 耶穌知道處於一個敵對神的世代而仍能忠心作見證人,這項工作十分艱鉅,因此賜下聖靈成為信徒內在推動的能源。一個沒有能源推動的見證人,就像車子的油缸沒有汽油,根本不能發動。(邏輯推理)
13. 「作我的見證人」表明這些見證人與耶穌有甚麼樣的關係?是屬於主的見證人?是有關耶穌的見證人?是耶穌差派出去的見證人?
• 按文法結構來說,「我的」應指到「有關我的」(witnesses that concern me),是說明這見證必須有關主的一生,祂的死與復活。(文法結構)
14. 耶穌在講完這句話之後升天,有甚麼重要性?
• 主耶穌交待一切之後,就在他們眼前被雲彩接去上升了。(上文下理)
• 耶穌升天之後,天使對門徒說:「…為甚麼站著望天呢?這離開你們被接升天的耶穌,你們見他怎樣往天上去,祂還要怎樣來。」(一11)天使提點他們不要停留或陶醉在這超然的經歷上,必須去實踐使命,直等到祂回來。(上文下理)
• 四福音裡亦有題述大使命的不同版本(參太廿八19-20;可十六15;路廿四47-48;約二十21)。耶穌在升天前再覆述一遍(徒一8),不單將聖工的籃圖劃出,亦將工作的範圍指定,讓門徒知道這是一項影嚮整個世界的使命(馬太福音亦早已題及「萬民」的字眼)。(比較經文)
15. 這節經文與使徒們往後的事奉有甚麼關聯?
• 這節經文已被公認為剖析使徒行傳分段結構的鑰節。由第一至第七章是門徒在耶路撒冷所作的見證(參路廿四47說:「從耶路撒冷起…」);第八至第九章是在猶太全地、撒瑪利亞所作的見證;而第十至第廿八章是從該撒利亞直到當時的「地極」所作的見證。(上文下理,文法結構)
**下期預告:請再看一遍以上的十五題答案,有那些比較難解的詞字或句語,需要對照註解,以保證所提出的答案不會離題。
可參考的使徒行傳註解包括:
• 布如司著,李本實譯,【使徒行傳】(近代萬國通用新約註解)。台北:浸宣會文字出版部,1969。
• 馬歇爾著,蔣黃心湄譯,【使徒行傳】(丁道爾新約聖經註釋)。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87/1997。
• 斯托得著,黃元林譯,【使徒行傳】(聖經信息系列)台北:校園書房出版社,1997。
• Barrett, C. K. A Critical and Exegetical Commentary on the Acts of the Apostles. 2 Vols. Edinburgh: T & T Clark, 1994.
• Longenecker, Richard N. “Acts” in The Expositor’s Bible Commentary, Vol. 9. edited by Frank E. Gaebelein, Grand Rapids, Michigan: Zondervan Publishing House, 1981.
忠於聖經又適切時需的釋經講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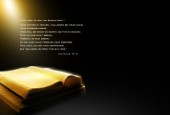 引言
引言
踏入二十一世紀後,整個時代都在急劇改變。面對種種變數,教會講道的模式,甚至講道的內容,是否須要作出相應的變更呢?還是以不變應萬變為佳?又到底在「萬變」中仍有「不變」的可能嗎?這些都是十分重要的課題,教會不能躲在四堵牆內,對外界的情況不聞不問。
一. 時代的衝擊
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我們正活在「後現代」的世界裡,這到底是甚麼意思呢?「後現代」的現象是從二十世紀末後的十數年所開始的,它一方面始於對「現代」所代表的真理觀、世界觀與人觀的質疑、批判與挑戰,另一方面卻又微妙地延續「現代」的一些基本假設。陶加理(David S. Dockery)描述後現代的人類面臨著「脫臼」(dislocating)的情況,原因是這時代傾向於使人類脫離固有的世界觀。1
假如「現代」世界是堅實可量度的硬地,「後現代」世界則是飄浮不定的大海;若是「現代」世界代表「秩序」與「結構」,「後現代」世界則代表著「虛無」與「混亂」。
正因為「後現代」的本質飄浮不定,要界定它並不容易,後現代的迷思便在於此。然而,我們可以根據一些普遍現象來指出它幾項較明顯的特徵。
首先,後現代主義對事物多方質疑。例如,他們對人生持悲觀的態度:人活著確實有終極的歸宿與意義嗎?他們對婚姻關係並不看好:在離婚率節節上升之際,結婚真的會比單身好嗎?他們認為,婚後二人能否堅持到底還是未知數呢。
其次,後現代文化其實是一種生活形態。它高舉感官,喜歡看具有影像的事物,過於抽象的理論。它強調人要有自由思考的選擇,做自己喜歡做的事,不要別人指定他們當怎樣行。因此,它有反權威的傾向。
最後,後現代主義強調世上沒有絕對真理存在。「現代主義」有一定的思維路向,是比較客觀的,可以預測的。然而,「後現代主義」卻吹無定向風,是主觀的、不能預測的。對於持現代主義的人來說,知識與真理是確定和可以掌握的。然而,後現代主義的人則認為,真理因人而異,不能被確定;真理經常受個人文化與背景的差異所影響而變質,因此沒有絕對的真理。
二. 面臨的挑戰
在後現代主義的衝擊之下,不少傳道者為要迎合會眾的「消費者心態」,在有意或無意之間,將聖經的教義淡出,將信仰的要求減弱,將信息的重點放在人的喜好上。傳道者只注意選取一些鼓勵人、安慰人的信息,刻意忽略那些責備人、警戒人、要人為信仰付代價的經文,因此給人一種「成功神學」或「悅樂福音」的錯覺。正因為傳道者沒有將神的話語原原本本、不折不扣地傳遞,以致將神的話語「邊緣化」而不自知。
再者,今日講道的時間有愈來愈短的趨勢,取而代之的是唱詩、見證、話劇或其他吸引人的節目等。凱沙(Walter Kaiser)早就看出這問題,他說:「無論人如何層出不窮地提出新的方法與重點,那唯一能使教會有活力、純真又有果效的,就是用更新的目標、激情與力量來宣講神的話語。」2其實,沒有甚麼事物可以取代根據神話語去宣講的地位。
三. 使命的承擔
傳道者是神的代言人,在講台上是代表神而不是代表傳道者自己。「講道」是神對人說話的時候,而講道者只是神的器皿。若是這樣,信息必須是從神而來,根據神的話語去闡釋神的心意。講道若沒有神的話語或偏離神的話語,神就不能成為一切的核心,會眾就容易崇拜人而不崇拜神了。
保羅早已預言人要厭煩純正真道的情況,然而,他仍向提摩太發出一項嚴峻的使命:「務要傳道」(提後四2)。這裡所要傳的「道」正是上文所論述的:神默示的聖經(提後三16-17)。保羅接著指出原因,說:「因為時候要到,人必厭煩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增添好些師傅。」(提後四3)「因為」這連接詞實在可圈可點。人通常的邏輯思維是:「若是別人不要聽,最好就不要講。何必浪費脣舌呢?」然而保羅的邏輯卻適得其反:「因為別人不要聽,你更加要講!」真是令人匪夷所思,似乎是一個不成理由的理由。
為甚麼人家不要聽,傳道者仍要傳講呢?理由十分簡單,因為有一天我們要向那審判活人與死人的主交帳(提後四1)。因為對神的託付不敢違逆,所以,即使面對一群不願聽道的會眾,傳道者亦不敢隨便放棄其使命。
聖經從來沒有說傳道者可以因應會眾的喜好而調整信息;相反地,傳道者乃是用神所託付的信息去調整會眾的生活形態。要在神面前作無愧的工人,就必須按著正意分解真理的道(提後二15);不是討人的喜歡,像當時的假師傅一那樣,採用迎合人的言論使發癢的耳朵感到舒服。
四. 釋經的講道
甚麼是忠於聖經、按正意分解的講道呢?近代的學者提出一個專門名稱──「釋經講道」。簡單來說,釋經講道是一種根據聖經而且有系統性的講道。透過傳道者生命的宣講,將聖經的信息帶進會眾的實際生活中。釋經講道是「心態」多於「模式」,意思是說,它不規限於某種形式,卻要弄清楚:「你是用你的思想去迎合經文呢?還是用經文去迎合你的思想呢?」3換句話說,講道者須弄清楚:「這是經文的意思?還是你將自己的意思加諸聖經裡?」
最好的測試是想像著摩西、以賽亞、保羅或彼得等人在場聆聽你講述他們所寫的經文,他們會對你所講的點頭稱是,說:「對!這正是我的意思。」還是會不斷搖頭說:「不是的!我從來沒有這樣說過。」
真正忠於聖經的講道者在這個時代只屬於少數民族。但感謝神,祂在這時代正興起一批傳道者,他們願意堅守聖經、宣講真道、逆流而上,這是可喜的現象。為甚麼不要迎合潮流,卻要在俗世洪流中形成為一股清流呢?有幾個原因叫傳道者必須這樣做。
第一,因為釋經講道建基在神話語的權威上。注重釋經講道的人,大多數是堅持聖經高度的權威(high view of Scriptures)。意思是說,他們堅信聖經絕對無誤,高舉聖經的權威,以聖經為真理的範本,並且願意服膺在真理之下。
第二,因為釋經講道可以有系統地傳達神的話語。釋經講道讓講者傳達神全備的啟示,使會眾得著全面與平衡的餵養。若只按講者的感動去講,他可能會來來去去只講自己喜歡講的題目,只選取自己偏愛的經文。至於聖經的重要書卷,以及有系統的教導,會容易被忽略了。況且,有系統的釋經講道,不愁缺乏題材,因為聖經是講不完的。
第三,因為神的話語是改變生命的唯一媒介。釋經講道是傳揚神的話語,而神的話語之寫成,目的主要是「叫屬神的人得以完全,預備行……」(提後三16-17),因此傳講神話語的主要目的同樣是要激發人活出真道。除了神的道,再沒有別的媒介可以達成這樣的目的了。釋經講道不是娛樂聽眾,或讓人感覺得比較舒服;釋經講道乃是藉著宣告神的心意,使人認識神,最終使人學像神,生命得改變。
五. 合宜的平衡
有人誤以為,釋經講道是一位學究般的講者站在講台上只知講解聖經,一點應用都沒有。另有人認為,釋經講道必定是死板沉悶、毫無生氣、與世隔絕、不吃人間煙火的講道。
上文已提述過,講道的主要的目的是要讓人認識神,然後生命得到改變。因此,「講道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生命」這句話包含著一個基本假設:生命的改變是因認識神與認識真理而來的。因此,在強調「生命改變」的同時,亦得注意改變生命的根據與基礎是神的話語;不能只注意「怎樣做」(How),而忽略告訴人這些行動所根據的是「甚麼」(What)。
由此可見,釋經講道最重要的兩個課題是:啟示(revelation)與應用(relevance)。前者是從神接受信息,後者乃將信息帶進會眾的生活中。這兩個課題在講道中必須產生適當的張力,因為忠於聖經的講道是與聽眾的生活息息相關,將天與地連接在一處的。正如一位德國神學家說:「一篇好的講道應該有天為它的父親,有地為它的母親。」
那麼,釋經講道是否要因應後現代的種種現象而多注意聽眾的情況呢?對於這個問題,答案可以是「要」,亦可以是「不要」。這話怎說?
澳洲講道學者莊士敦(Graham Johnston)在他所寫的一本論講道的書中,引用蘇瑪克(Samuel Shoemaker)的一首詩說明他講道的進路:「我站在門前,不是深入在門裡面,亦不是離開門外很遠。這門是世界最重要的一道門,是人認識神與進到神面前的門。」4這首詩正好說明莊士敦對講道的進路。他認為傳道者必須站在門的旁邊,不要太深入在門裡面,因為若太深入,就不能接觸後現代的聽眾。他用這幅圖畫說明傳道者要認識時代,所講的是後現代人能明白的話語。
其實,後現代主義與基督徒信仰的對話不全都是負面的。後現代主義者追求一個可以體認的信仰,不是不切實際的理論。因此在講道的時候,傳道者必須讓他們看見神話語的活潑(來四12),而且採用他們可明白的語言、實際的經歷與嶄新的圖畫,將神確切的話語予以詮釋。
但我們要小心,不可以將內容變更以遷就聽眾;不是因為他們要聽甚麼,講者就提供甚麼。講道是唯一不能受到「市場剌激」(market driven)而將「產品」改頭換面的。在這末後的世代中,人雖然厭煩純正的真道(原意是「健全的真道」),傳道者仍要講。不然,若只知嘩眾取寵,傳道者就會容易墮入亞倫的錯謬中──為要迎合會眾的要求,成了現代金牛犢的製造者,以它代替神在教會中唯一配受敬拜的地位。
如何正確解釋【聖徒復活】及相關問題?
耶穌死的時候,耶路撒冷城內有聖徒復活(太二十七52-53),這些人是誰?他們比耶穌先復活是否會影響耶穌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十五20)的教義?
讓我們先看有關的經文:
51 忽然,殿裏的幔子從上到下裂為兩半,地也震動,磐石也崩裂,52 墳墓也開了,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53 到耶穌復活以後,他們從墳墓裏出來,進了聖城,向許多人顯現。54 百夫長和一同看守耶穌的人看見地震並所經歷的事,就極其害怕,說:「這真是神的兒子了!」(太二十七51-54)
這事蹟只有馬太記述,而未見載於另外三卷福音書。相信馬太要藉著見證幔子裂為兩半、地大震動、磐石崩裂、聖徒復活,以及百夫長與看守之人的回應(二十七51-54),證明耶穌是彌賽亞,是神的兒子。
在這些現象中以「聖徒復活」最具爭議性,引發一些解釋上與神學上的問題。
這些聖徒到底是誰?相信他們是舊約的聖徒。那麼,是舊約的全部聖徒嗎?應該不是。因為經文說:「已睡聖徒的身體,多有起來的」,是部分而不是全部,但人數多少則不得而知。他們復活之後就在耶路撒冷及附近地區顯現,作耶穌之身分與工作的見證。這樣解釋十分配合馬太福音寫作的主題。
他們在甚麼時候復活呢?是在耶穌死的時候(參太二十七50,及51-52節)。和合本說他們在耶穌死的時候復活,等到耶穌復活之後才進城顯現給人看(53節),意思是:在他們復活與顯現之間,有一段時間停留在墳墓裏。當然,這樣解釋按原文語法是可行的。因「到耶穌復活之後」這短語,可以指他們「到耶穌復活之後」才「起來」,或是「到耶穌復活之後」才「進城」,二者均可。
其實,這兩種解釋在意義上相差不遠。後者是要指出他們在耶穌死的時候復活,但等耶穌復活之後才進城;這樣解釋可以避免一個難題,就是他們在耶穌復活之先有所行動。但無論怎樣,他們畢竟比耶穌先行復活,只不過在墳墓裏停留,仍未能印證耶穌是「從死裏首先復生」(西一18),以及祂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林前十五20)等教義。另外,他們留在墳墓裏做甚麼呢?若沒有事情可做,為甚麼不在耶穌復活之後才復活,偏要在耶穌死時復活呢?
因此,最合理的解釋是:他們的復活是指「普通的身體」復活,沒有「榮耀的身體」(參林前十五43)。這正好像耶穌在傳道期間曾使拉撒路(約十一43-44)、拿因城寡婦之子(路七13-15)與睚魯的女兒(路八52-56)等人從死裏復活一樣。這些人復活之後,在世上活了一段時間,但最後仍要經歷死亡,與常人無異。因此,已睡聖徒那「普通的身體」復活雖然先於耶穌「榮耀的身體」的復活,卻不會影響耶穌是「睡了之人初熟的果子」的教義。
這些聖徒在耶穌死的時候復活,要表明甚麼屬靈的意義呢?相信是要證明耶穌的死不是常人的死,而是與救贖計劃息息相關的死。因此在祂死的時候,有幔子裂為兩半、地大震動、磐石崩裂與聖徒復活等超然現象伴隨。有解經學者說得好:「耶穌的死與復活的生命息息相關。在祂死的時候,死人因祂的死而復活;當祂由生入死的同時,這些聖徒亦得以由死入生。」(W. D. Davis & Dale C. Allison Jr. Matthew, The International Commentary Series, III: 633)
背誦經文 – 在基督裡的屬靈地位
一. 我屬靈的地位
- 我是神的兒子(約一12;弗一5)
- 我是蒙赦免的人(西一14)
- 我因信被稱為義(羅五1)
- 我是新造的人(林後五17)
- 我是聖徒(林前一2;弗一1;西一2)
- 我是被主用重價買來的(林前六19-20)
- 我在基督裡受聖靈的印記(林後一21-22;弗一13-14)
- 我是天國的國民(腓三20)
- 我是神的傑作(弗二10)
- 我已經與主聯合(羅六3-4)
- 我永不再被定罪(羅八1-2)
- 我不再受惡者的控訴(羅八31;約壹五18)
- 我是基督的朋友(約十五15)
- 我與基督一同被藏在神裡面(西三3)
- 我與基督一同坐在天上(弗二6)
二. 我生命的功能
- 我是世上的鹽(太五13)
- 我是世上的光(太五14-16)
- 我是被揀選要結果子的(約十五1、5、16)
- 我是基督的見證人(徒一8)
- 我是神人之間的和好使者(林後五17)
- 我是與神同工的(林後六1)
- 我是神的管家(林前四1-2)
- 我是基督身體中的肢體(羅十二4-5;林前十二27)
- 我是基督的薦信(林後三3)
士師記十四章4節中的「他」是指參孫嗎?
這裏的「他」應該是指耶和華神,不是參孫。多個聖經譯本與註釋書的主張都是如此。
但有人卻認為,參孫是信心的偉人(來十一32),他娶非利士人的女人為妻,是要藉此機會攻擊非利士人。再看參孫的生平,他確實是在找這樣的機會(參士十五3)。作為拿細耳人的參孫,雖然生活隨便,但不能因此否定他的信心和作為士師的使命。
另外,士師記第十四至十七章的主語大多是參孫。在十四章4節開始時提及「他的父母」,當中的「他」顯然是指參孫;在同一節而且在同一個句子中,前面的「他」指參孫,而後面的「他」指耶和華,這種闡述似乎說不過去。
在解經的原則裏,較為重要的應該是上文下理與文法結構。若按經文的文詞語句去理解,這裏的「他」解釋為耶和華比較合理。雖然前一分句的「他」是指參孫,但後一分句「因為他找機會……」中的「他」卻是指代前一分句尾的「耶和華」,意思是耶和華神找機會要攻擊非利士人。當然,參孫可能有同樣的意願 (參士十五3),但那並非這段經文的重點所在。若按文法的鋪排,要另下結論就比較困難。
參孫雖然是信心偉人 (來十一32),然而,不能用這個結論去推論他一生所作的都是信心的表現。他這次要娶非利士女子為妻,主要是基於他個人的喜好與肉體的情慾,因他對父親說:「願你給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悅她」(士十四3下)。
參孫不聽父母的命令(士十四3上),他亦沒有將神的律例放在眼內。神在舊約律例中清楚定規,以色列人不能娶外邦人的女兒為妻,恐怕他們會因此隨從她們敬拜偶像(參出三十四12-16;申七3)。參孫卻一意孤行,只順從低下的慾望行事。
請再看士師記十四章4節,這句話是這卷書的作者加上的評語,說明事件背後的原因。雖然參孫行他自己眼中看為正的事,要娶外邦女子為妻,但神卻「破格」容許這件事發生,以成全祂的心意。神的旨意確實高過人的旨意,神的道路高過人的道路。
十步釋經法之如何提出解釋性問題?
 我與讀者曾探討如何將觀察所得的原料轉化成觀察問題,並在適當時候,將觀察問題再跟進寫出解釋性問題。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集中討論如何設計並提出解釋性問題。
我與讀者曾探討如何將觀察所得的原料轉化成觀察問題,並在適當時候,將觀察問題再跟進寫出解釋性問題。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集中討論如何設計並提出解釋性問題。
解釋性問題大致可分為三類:求知的問題、因果的問題與求證的問題。茲用創世記二十二章1至19節亞伯拉罕獻以撒為例予以說明。
一. 求知的問題
「求知的問題」之目的,是要找出詞句的定義或經文難以理解的地方。它基本上要尋求以下問題的回答──「作者這樣記述到底是甚麼意思?」。
*例證1:神既是無所不知,為何祂會說「現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12節)?
這裏的「知道」並非表示神在之前並不知情,而是採用「擬人法」,用人可以明白的言詞,說明亞伯拉罕如何藉著順服的行動去表明他敬畏神。這句話同時道出神對亞伯拉罕之行動的接納與嘉許。
*例證2:為該地方起名叫「耶和華以勒」(14節)的用意何在?
「耶和華以勒」的意思是耶和華必預備。亞伯拉罕為那地方起名,是一項感恩的舉動,讓後世的人知道神是豐富且必供應人所需要的。
二. 因果的問題
「因果的問題」之目的,是要徹查經文中詞句或短語的因果關係,特別針對經文中不協調之處或因果關係不明顯之處。它基本上要尋求以下問題的回答──「它們之間有甚麼因果上的關係?」或「是甚麼原因導致這樣的後果呢?」。
*例證1:「這些事以後」(1節上)是指甚麼事呢?又「神要試驗亞伯拉罕」(1節下)甚麼呢?
「這些事之後」是創世記經常出見的連接句,目的是要將敍事文各段落彼此的關係連接在一起。由於這處經文沒有明確指出上文的那些事情,故此我們只能籠統地說它包含著第二十二章之前所發生的事。從這句短語可見,亞伯拉罕這時候的屬靈光景已經足以應付這一類的重大試驗。
「神要試驗亞伯拉罕」是「總括性用語」,指出了記述緊隨著之敍事文的目的。神要試驗亞伯拉罕甚麼呢?相信是要試驗他的順服,要看他是否愛以撒過於愛神。經文三次強調以撒是他「獨生的兒子」(2、12、16節),提醒他這次奉獻的難度;又從後來神的使者宣告說:「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18節),可見「順服神」顯然是這試驗的目的。另外,這事件亦包括對亞伯拉罕信心的考驗,看他對神一直以來給他的應許──「你的後裔必眾多」──是否堅信不移。
*例證2:神吩咐亞伯拉罕將以撒獻上,是否過於殘忍?
要求將兒子獻上為祭確實是十分殘忍的事。但前一個問題必須從兩個層面來看。
先從結果來看,神最終並沒有要以撒死,故此那「殘忍」的情況並沒有出現。在這次試驗中,神所要的其實不是以撒,乃是亞伯拉罕。最後峰迴路轉,神將以撒歸還給亞伯拉罕。因此,並不算是殘忍。但從整個過程來看,亞伯拉罕是有血有肉、有親情的人,要自己親手殺死自己的兒子,這個意念在那三天內不斷盤旋在腦海中,那是無情的煎熬。因此,從這個角度看,神吩咐亞伯拉罕做的事是十分殘忍的。
三. 求證的問題
「求證的問題」之目的,是從兩個或以上的結論中探討何者比較合理。它基本上要尋求以下問題的回答──「這兩個看法中,哪一個比較合理?」或「有甚麼經文的佐證支持這樣的結論?」。
*例證:亞伯拉罕顯然知道此行是要將以撒獻上,但卻對僕人說:「你們和驢在此等候,我與童子往那裏去拜一拜,就回到你們這裡來。」(5節)這樣說是否有說謊之嫌?
這句話可有下列不同的結論:
1. 亞伯拉罕具有充足的信心,相信他與兒子必定能回來。
2. 在緊急的情況下,亞伯拉罕只是找些話來搪塞過去,他自己並不知道在說些甚麼。
3. 這是一項連他自己也無法完全體會的預言。
從亞伯拉罕後來對以撒說「神必自己預備作燔祭的羊羔……」(8節),足以證明他對神具備充足的信心,故此他對僕人說了那句話。他不願意帶僕人同往,也許是因為僕人不一定能認同這次行動,他們同行反而會使情況變得複雜。如此看來,第1個結論比較合理。
基督徒到天堂之後,要晝夜讚美,那豈不是十分沉悶的事嗎?果真如此,在地上的生活豈不是更具有多樣性與挑戰性?
基督徒將來到了天堂,無可置疑,讚美與敬拜是主要的事奉。
啟示錄是一本論述世界終局的書,它在討論地上大災難的同時,亦多次穿插著描述天上敬拜的情景(參啟四8、10-11,五9-10、12-14,七9-10、11-12,十一15-18,十四1-5,十五2-4,十六4-7,十九1-6)。從這些經文,我們可見到幾項基本事實:
1. 天上的敬拜少不了天使與四活物的參與(啟四8,七11-12,十一15,十六4-7)。
2. 除了天使之外,蒙救贖的群體亦有分在天上的大敬拜聚會中(啟五13-14,七9-10,十四1-5,十五2-4,十九1-6)。若「二十四位長老」被解釋為蒙救贖者的代表,那麼經文的出處可以加上啟四10-11、五8-10、七11-12及十一15-18。
3. 敬拜的對象是坐寶座的父神與曾被殺的羔羊耶穌基督(敬拜父神:啟四2-6,七11-12,十一15-18,十四1-5,十五2-4,十六4-7,十九1-6;敬拜羔羊:五6-10、11-12;敬拜父神與羔羊:五13-14,七9-10)。
4. 在這些敬拜的描述中,有三處提及他們歌唱敬拜:啟五8-9(四活物與二十四位長老唱詩歌);十四1-5(蒙救贖者唱別人不能學的新歌);十五2-4(勝過獸的人唱摩西的歌和羔羊的歌)。
由此可見,聖徒在天上確實會與天使一同參與敬拜,並且用詩歌頌唱歸榮耀給神。至於是否「晝夜讚美」,則不能確定。假若敬拜是聖徒在天上要經常做的事,那是不是一件沉悶的事呢?這個問題可分述如下:
首先,我們得承認地上的人不能完全理解天堂的生活。正如一個人站在河的這一邊,不能完全明白河另一邊的人怎樣生活。雖然聖經有提述天堂生活的情況,但那只是在頭腦上的理解,與實際的經歷還有一段距離。有些宗教試圖用肉體的感官去投射,認為將來在「天堂」裏會有醇酒、美人與各樣物質的享受。然而聖經清楚地記述,屬血氣的人不能承受神的國(林前十五50;加五19-21),聖徒要得著永恆的祝福,必須經常改變,得著榮耀復活的身體才可以領受。千萬不可以從物慾的角度去理解天上的經歷。
第二,用肉身軀體的觀念,同樣不能瞭解如何能晝夜(或經常)唱詩讚美,因為我們的身體要睡覺,而且我們的喉嚨不能容讓我們不停地歌唱。然而,聖徒將來得著榮耀的身體之後,即使晝夜讚美也不會感到口乾或疲乏。
第三,地上教會的讚美與敬拜,亦無法與將來天上的相比。許多教會因為人數不多,加上大部分會眾唱詩提不起勁,故此不能產生一種令人嚮往讚美與敬拜的效果。將來與千千萬萬的聖徒和天使一同敬拜,那種震撼力非同小可,必定不會沉悶。
最後,地上的敬拜可能會缺乏主題,但在天上並不缺乏,因為所唱的都是「新歌」(啟五9,十四3)。「新歌」的意思不單是曲調上的新,更是主題上的新,是從生命的體驗中唱出來的。若不是在蒙救贖的人群中,這新歌是學不會的(啟十四3)。聖徒在天上愈讚美,就愈發現神本性的一切豐盛與美善,直到永遠仍有讚美不完的主題。
啟示錄十四章1至5節用「守童身」與「未曾沾染婦女」來描述蒙救贖者與主之間的關係,相信這是用許配給基督作新婦的背景而寫成(參林後十一2;啟十九7-10)。故此,我們可以用婚姻的關係去理解所提出的問題。不少青年男女在戀愛期間都有切慕對方、震人心弦的感受。他們經常想念、渴望與愛人在一起。當二人共處時,就有說不完的話題,有時候雖然無話可說,亦可以達到「無聲勝有聲」的境界。若是環境與體力許可的話,雙方二十四小時在一起亦不會感到沉悶。
我相信將來在天上的讚美與敬拜不會沉悶,因為我們將來得著榮耀的身體,加上神的屬性讓我們有唱不完的主題,再加上對主的愛慕,那必定是一種可以持續到永遠的享受。故此,天堂是不是一個沉悶的地方,全在乎你與坐寶座的父神與羔羊耶穌基督之間的關係如何。
天堂實在是音樂的城、讚美的城、歌頌的城。若將來在天上的生活主要是讚美與敬拜,那麼我們現在最好多學習讚美、敬拜主;不然,到了天上可能會有「水土不服」的現象出現。
如何解釋摩西「離開埃及,不怕王怒」?
摩西「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可有兩種不同的解釋。
摩西「因著信,離開埃及,不怕王怒」(來十一27)可有兩個不同的指向:摩西第一次逃離埃及,或第二次出埃及──他帶領著以色列人離開的。引發第二種解釋的主要原因,是因為在出埃及記二章14至15節的記述中,摩西是因為懼怕而逃離埃及,與信心拉不上關係。他後來領以色列人出埃及比較上算是出於信心,故此有這樣兩種不同的看法。
首先,讓我們看第二種解釋,即認為來十一27是指摩西後來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
支持的理由如下:
1. 摩西在打死埃及人之後離開埃及,明顯地是與他的「懼怕」有關(出二14),談不上是「因著信」而離開(來十一27)。
2. 摩西後來帶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在法老王多方阻撓與威嚇之下,仍然持定信心,不怕王怒,力挽狂瀾,終於成功地完成託付。這與「因著信,就離開埃及,不怕王怒」在邏輯上有直接的關係。
3. 若是指向摩西第二次出埃及,希伯來書十一章23至29節就可分為以下三個重要時期:
(1) 從出生到成年(23節)
(2) 殺埃及人、離開王宮、到米甸曠野(24-26節)
(3) 領以色列人出埃及(27-29節)
其次,讓我們看第一種解釋,即認為來十一27是指摩西離開埃及到米甸曠野。
支持的理由如下:
1. 若認為希伯來書十一章27節是論述摩西後來領以色列人離開埃及,就會與來十一23-29整段的語法結構互相牴觸。因為整段經文有五個「因著信」的短語,都指向摩西生平一個重要時段:
(1) 摩西的父母「因著信」,將摩西藏了三個月(23節);
(2) 摩西「因著信」,不肯稱為法老女兒之子(24節);
(3)「因著信」,他離開埃及(27節);
(4)「因著信」,他守逾越節(28節);
(5) 他們「因著信」,過紅海如行乾地(29節)。
2. 「不怕王怒」與摩西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實際情況不能協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時,法老王與埃及人因為看見耶和華神藉著十災所施行的權能,都懼怕摩西與以色列人,巴不得他們能早日離開,這點與摩西「不怕王怒」的描述剛好相反。
至於出埃及記二章14至15節,經文雖然沒有說法老王「發怒」,卻記載說「法老……就想殺摩西」,想殺摩西當然是因「發怒」而產生的念頭。除了出二14-15之外,在殺埃及人事件與逃離埃及的期間,找不到別的經文述及法老王對摩西發怒。「怒」從何來?須有個交代;否則,經文的解釋會很牽強。
3. 第一種解釋的難解之處,是怎樣將摩西逃離埃及時的「懼怕」解釋為「信心」的表現。這問題可從兩方面探討:
一方面,出埃及記二章14節是局部性的描述,希伯來書十一章27節則是全面性的描述。出埃及記說摩西為自己的安危感到害怕;但希伯來書強調他在這次離開埃及之前,如何選擇事奉神而不事奉法老,並詳細交代他不願被稱為法老女兒之子的原因(24-26節),然後才說他離開埃及(27節上)。然而,他離開埃及不是因為懼怕,而是因為渴慕得著那更恆久的賞賜(27節下)。希伯來書的作者歸納整個事件,看出摩西的勇氣、信心以及對神的忠誠。
另一方面,摩西在殺死埃及人之後,經文記述他「懼怕」(出二14);他後來「躲避法老,逃往米甸地居住」(二15)。然而,兩節經文在時間上與邏輯上不一定是緊接在一起的。「躲避法老」可以是往後發生的事,與「懼怕」沒有直接關係。希伯來書作者將兩件事情分開討論。
總結來說,若從經文的上文下理與語法結構來看,摩西「離開埃及,不怕王怒」最合理與最自然的解釋,應該是指他第一次離開埃及說的。
在選取合理解釋的過程中,看經文的「上文下理」應是首選的原則,這與「語法結構」是密切相連的。因為經文多次出現「因著信」這短語,所以它可作為結構的分界。
另外,聖經作者不一定將事件所有細節都詳加記錄。當兩段經文有不協調的記述時,不要立刻下結論說它們互相矛盾;它們可以是互相補充,從不同的角度切入。當然,這不是平時可以容易讀出來的。正因為這樣,當兩段經文產生矛盾時,我們必須從其中找出合理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