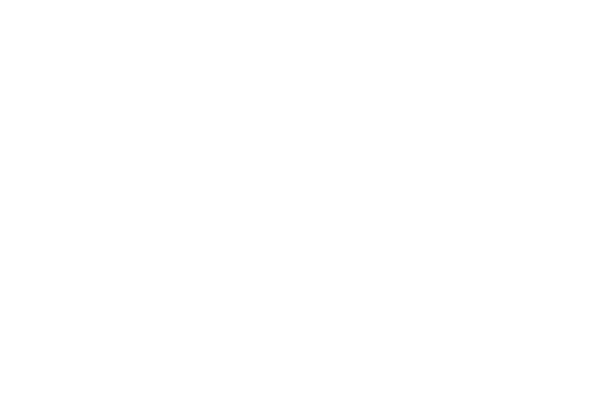藝術與色情如何分界線?
現時流行的坊間藝術,包括潮流音樂、小說、廣告設計、電影、動畫、繪畫、插畫、戲劇、逗笑秀、裝置、舞蹈等,都是表達人生以及思想感情的最佳媒體;既是表達人生的載體,與性相連的東西是不可避免的,無論是正常與不正常的內容,都直接或間接涉及性,因為生與性相連。然而,創作藝術的人,到底如何分別藝術作品與以負面的色情充當藝術的作品呢?欣賞藝術的人,又如何分辨呢?在學術上,這是美學與道德的問題。雖說任何事物都可以引起色情的聯想,但我們不能認為,必須把所有藝術作品都放在道德的顯微鏡下作分析。不過,作為公眾的藝術作品,無可否認擁有媒體必然擁有的影響力,對大眾社群不可避免的產生巨大的塑造力和滋擾力,免不了與道德標準掛鉤,因作品會刺激起大眾的道德意識,使人不得不有所反應。
一個常觸及的問題是:常常接觸以“色情或暴力”為主題藝術作品的觀眾,是否易受不良的道德影響呢?這是屬於相當貼身的問題,需要在心理學與社會學的層面進行實驗和研究。另一個問題是關於審查:含有低劣道德性的作品,是否應該接受打壓?這涉及個人的表達自由,屬政治哲學的範疇。以上的兩個問題不是本文要解答的。本文要處理的,是關於藝術與色情的分野問題,這問題所涉及的因素相當複雜,如作品的內容與形式(審美)的配合、創作力、媒體的運用、想像空間等。高度引起不安和難以接受的作品是顯而易辨的,問題在於那些介乎藝術與色情之間的作品,我們如何分辨?我們要知道,藝術若要真實的表達人生,或多或少涉及情慾,而人的想像空間中亦存有情慾之事,如肯尼斯.克拉克(Kenneth Clark)所言:“任何一個祼像(nude),無論它如何抽象,從來沒有不喚起觀者的零星情慾(即使是最微弱的念頭)。如果不是這樣,它反而是低劣的藝術,是虛偽的道德。”
但是,扭曲性慾,濫用性為主題,以性的吸引力,假借藝術形式來兜售色情,以為藝術只是一種審美形式,當中不含任何道德評價和取向,這是一種極天真的想法。純藝術形式主義者都不能在表達畸形情慾鏡頭的銀幕前,進行只有屬於“色彩、剪接、統一、構圖、形象”等純形式的審美觀賞,而不考慮道德成份於藝術評價上影響,尢其是屬於公開,並觸及大眾思維和感受的作品。
雖然孰是藝術、孰是色情,兩者本身已具相當的不穩定性,不能抽離社會群體來定義。
第一,可因人而定:甚麼是藝術?可因無知識而視而不見,不懂藝術,因此無動於衷;甚麼是色情?可因慣性被色情的東西所包圍而失去知覺;亦有人會過於保守,不能接受任何有關於肉體的東西,甚至在藝術中對情愛的描述,也不能接受。因此,道德主義易把藝術欣賞的水準拖低。亦有人過於膚淺,或只求新奇,甚麼都可以算是藝術。
第二,顯而易見:因為“含蓄又樂而不淫的”與“露骨淫穢突兀的”是明明可分的,但亦可因慣性心態而失去辨識力。
第三,因文化和地域的改變而有所不同,今日的尺度與維多利亞時代的尺度有異:衣著、談話、行為,連帶性觀念與藝術的觀念,都起很大的變化。
為藝術與色情定下界線,古人有很好的提示。劉勰(466-539)於《文心雕龍.宗經》指出:“(佳美的藝術作品的標準是:)情深而不詭,風清而不雜,事信而不誕、義直而不回,體約而不蕪,文麗而不淫。”意譯為“感情深摯而不虛假,作用純正而不雜亂,事例真實而不荒誕,義理正確而不歪曲,體勢精約而不繁雜,文辭華麗而不過分。”這六個優點指出一個方向,凡是無病呻吟、浮誇的、粗榻的、粗糙的、濫情的、炫耀技巧的,都不是好的藝術。這對創作者與欣賞者而言,都是很好的指引。實際上,真、善、美的確難以區分。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時代。基督徒當如何在這世代中追求美好的靈性呢?
二十一世紀是一個十分複雜的時代。基督徒當如何在這世代中追求美好的靈性呢?